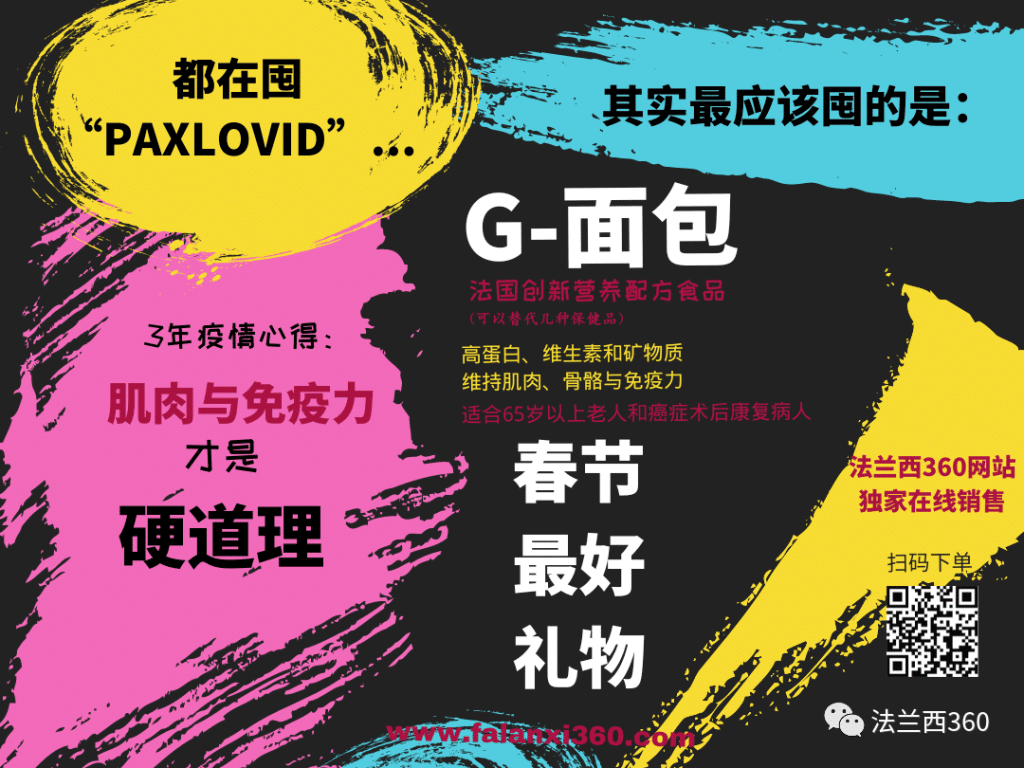时代的厌食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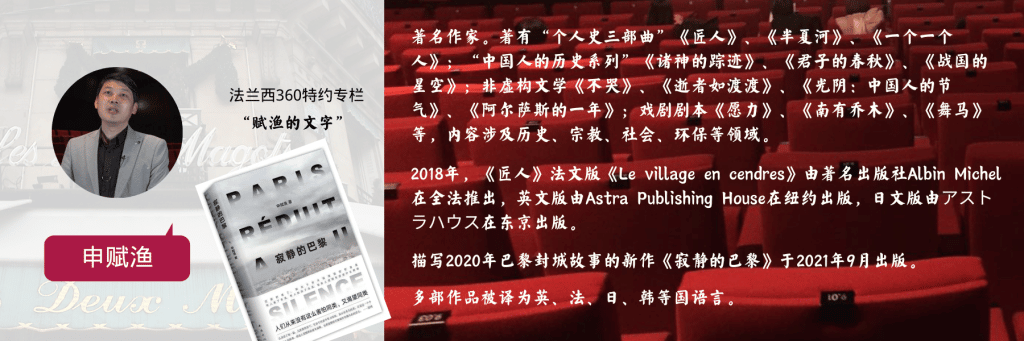

米勒《晚祷》(摄于巴黎奥赛博物馆)
我的一位法国朋友的女儿得了厌食症。几年前我在他家过圣诞节,见过这个女孩,活泼漂亮,开心地给我们唱圣诞歌,她爸爸用吉他给她伴奏。现在,这个刚刚十八岁的女孩不吃饭了,她说自己太胖。
她都不敢照镜子,镜子里的那个自己不能看,胖得太厉害了。医生说,你照照镜子,把你看到的样子画出来。她照了,然后在纸上画了出来——一个出奇的大胖子。医生在地上放了一张纸,让她躺在上面,让她妈妈把她的轮廓画下来。女孩根本不相信妈妈画的,妈妈画的不是真实的她。她仍然不肯吃饭。
这个女孩已经瘦成皮包骨头,形同骷髅。可是她看不到自己真实的样子,她也不相信这个所谓真实的自己。她心里有她确认的那个胖姑娘,她觉得自己胖得可怕。妈妈说,再不吃饭,她就要死了。她就不吃。
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,我无比吃惊。难道我们的眼睛,看到的并不是真实?难道我们看到的世界与别人所见迥然不同?难道对于不同的心灵来说,有着不同的世界?什么是真实的?什么是虚幻的?这个女孩的眼睛到底看到了什么?眼睛把什么告诉了自己的内心,还是内心就照自己理解的样子告诉了自己的大脑?
我一时对自己的眼睛失去了信心,随后对我的心也产生了疑问。我的所见都是事实吗?我的所知都是真理吗?我所坚持的都是正义吗?我的额头冒出了汗,也许,我的境况并不比这个得了厌食症的女孩好多少。
我的公寓斜对面那幢楼的二楼,是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工作室。雷诺阿、莫奈、德加、毕沙罗、莫里索等人常来这里聚会。二楼的窗户总是关着,在夕阳西下的时候,会把落日的余晖反照到我们这幢楼前的小街上。是他们,是窗内的那些人,解放了我们的眼睛,把我们的眼睛从造型、线条和构图中解放出来,从题材、结构和细节中解放出来,让我们看到了色彩和光线。在此之前,我们的眼睛是瞎的,或者说是半盲的。
我每天散步经过的罗马路上,住着桂冠诗人马拉美,马拉美每周二在家里举办沙龙,这就是艺术史上有名的“马拉美的星期二”。马拉美的楼下立了一个铜牌,表明这里已经成了历史遗迹。音乐家德彪西是这里的常客。就是这位先生,解放了我们耳朵。他打破了我们听觉的惯性,剪断了音乐的线条,从错综复杂的乐声当中,采撷出颤动的色彩和爱抚的情调。也是从这一刻起,我们终于在音乐当中听到了自然的声音。我们听到了钹不是哐铛哐铛地撞击,而是边缘的轻轻碰触。我们听到的不是轰隆的鼓声,而是被厚厚蒙了一层之后的情绪的震动。小提琴、三角铁、竖琴,各自发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清澈的音色和情感,我们轻易就能一一辨认,我们的耳朵随之起舞。
继眼睛和耳朵解放之后,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解放。打开心灵的那只神经质的手,是普鲁斯特的。在普鲁斯特之前,我们并不能真切地知道我们的心有多少个层次,有着怎样的百转千回,有着如何的细致与曲折。只有在普鲁斯特之后,我们才清晰地知道,外面的世界有多宽广,内心的世界就有多深邃。普鲁斯特在世的时候,就被一家银行从住处驱逐了。他离开不久就死了。现在他的窗户底下,假惺惺地嵌了一个水泥牌子,上面说何时至何时,普鲁斯特先生曾在此居住云云。我许多个夜晚从这里经过,窗下那张长椅上常常有人沉默地靠在上面。那个窗里的人,总能说出我们说不清的悲伤和说不出的痛。
现在,我们的眼睛已经看不到真正的色彩。那些人在画布上涂抹着自己的无聊、卑怯和空虚。我们的耳朵里更多的是毫无意义的噪音或者胁肩谄笑的颂扬。我们放任着自己的心灵,让它一点点变得麻木、冰冷而死寂。我们慢慢坚信所见所闻都是真的,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偏执的念想,一如厌食的女孩在镜中看到自己肥胖得不成体统。
马奈、德彪西、普鲁斯特,做了一百年前他们该做的事,他们早已消失不见。过了“一战”,过了“二战”,世界又开始变得贪婪、阴险、混乱和血腥。真相就在那里,人们却成了哑巴。每天晚上,我都焦躁地徘徊在巴黎街头,从一扇扇曾经的智者和如今俗人的窗口下走过。这里的繁华远胜于从前,似乎每一个窗口都是生活的温暖和希望。这里看不见战争的炮火,听不见瘟疫下的呻吟,也感受不到世界的撕裂、动荡、衰败和崩溃,这里厌弃所有不好的消息,没有一个人推开窗户大喊:“醒醒吧,这个世界病了,我们都已经是精神的骷髅。”
–申赋渔–
作家,现居巴黎。著有“个人史三部曲”(《匠人》、《半夏河》、《一个一个人》),“中国人的历史系列”(《诸神的踪迹》、《君子的春秋》、《战国的星空》),《寂静的巴黎》《阿尔萨斯的一年》《光阴—中国人的节气》《不哭》《逝者如渡渡》等多部作品。《匠人》法文版由Albin Michel在巴黎出版,英文版由Astra Publishing House在纽约出版,日文版由アストラハウス在东京出版。多部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日、韩等国语言。
以下是本站广告